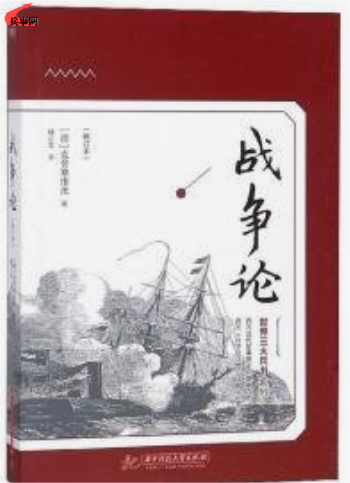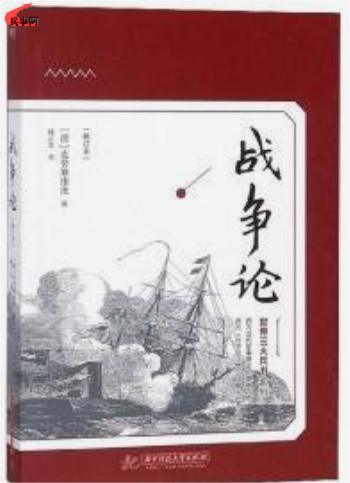政治目的对战争目标的影响 战争是政治的一种工具·第六
出自————《战争论》《战争计划·第八》
出自————《西方军事著作》
一、政治目的对战争目标的影响
一个国家对待另一个国家的事情象对待自己国家的事情那样认真,那是永远不可能的。
在其他国家有事时,它也只能派出一支数量较小的援军;假如这支援军失利了,它也就认为自己已尽到了援助的责 任,于是就会尽可能地寻找各种理由以利于脱身。
在欧洲政治中一贯地有一种惯例,那就是加入攻守同盟的国家必须要承担相互支援的义务。但是,一个国家并不因此就一定同另一个国家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它们考虑的并不是战争的对象是谁和敌人使用兵力的多少,只是相互事先约定派出一定的、一般为数非常有限的军队。在执行这种同盟义务时,同盟国并不以为他们与敌人已经处于必须以宣战开始和以缔结和约而告终的真正的战争中。而且,就是这种观念也并不是在一切情况下都非常明确的,它在运用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如果同盟国能够把约定提供的一万、二万或三万援军全部交给正在作战的国家,让它根据他自己的要求来使用,让它能够把这支援军当作是雇来的部队,那么,事情就会有了某种内在的联系,战争理论在这方面也就能够完全陷入束手无策的境地了。然而,实际上事情并非象想想的那样。援军一般都有自己的统帅,统帅只遵照本国政府的意志行事,而本国政府给他制定的目标,总是和政府的不彻底的意图是一致的。
甚至当两个国家一起与第三个国家真正进行交战时,这两个国家也并不都是必然的会把第三个国家当作不可调和的敌人,它们往往会象做生意那样地行事。每一个国家都会依根据自己可能冒的风险和可能获得的利益投入三四万人作为股金,而且表示在这次交易中除了这点股金外不会再承担任何责任。
不仅是一个国家为了一些对它本国没有任何切身利益的事情去支援另一个国家时是这样,甚至当两个国家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很大的共同利益时,支援也不是毫无保留的。而且同盟者一般也只是按照事先的约定提供条约规定的少量援助,而把其余的军事力量保留起来,以便将来依据政治上的特殊考虑留作备用。
这种对同盟战争的表现是非常普遍的,只是到了现代,当特别的危险迫使一些国家(如反抗拿破仑的国家)走上自然的道路时,当毫无限制的暴力战争迫使一些国家(如屈从于拿破仑的国家)走上这条道路时,才不得不采用自然的态度。过去那一种态度具有不彻底性,是不正常的,因为战争与和平在本质上是两个不可划分阶段的概念。但是,这种态度并不单单出现在理性所不齿的、纯粹的外交习惯方面,而且也渊源于人类所具有的局限性和弱点。
最后,就是在一个国家独立地对其他国家进行的战争中,战争的政治原因对战争的进行也具有很强的影响。
如果我们只希望敌人做出不大的牺牲,那么,我们就会对通过战争取得一个不大的等价物而感到满足,而且我们会感到,经过不大的努力就能够达到这个目标。敌人大致上也会作出相同的考虑。一旦这一方或那一方感觉到自己的考虑不是很正确,发现自己不象本来想象的那样比敌人强大,而是比敌人衰弱,他一般就会感觉到军费的不足和其他各种手段,在精神上就会缺少能够激起较大干劲的力量。因此,他只能尽力地应付,希望将来出现对他有益的事件(虽然他这种期望是毫无根据的),在这样的情形下,战争就好象是一个久病的人一样毫无生气无力地勉强拖延着。
这样一来,战争中的相互作用,每一方都希望战胜对方的竞争、暴烈性和无节制性,都消失在微弱的企图所引起的停顿状态中,双方都不会冒着战争的危险在大大缩小了的范围内进行活动。
假如我们承认(其实也不能不承认)政治目的对战争能产生如此的影响,那么,这种影响就不再有什么界限了,我们甚至不得不承认还存在着目的只是作为威胁敌人的手段以便用来支持谈判的战争。
假设战争理论要成为而且一直成为哲学的探讨,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它显然就会处在无计可施的境地。它在这里找不到能够含概战争概念中的所有必然的东西,因此它就会丧失掉它所能成立的一切依据。尽管如此,不久就有了一条自然的出路。在军事行动中缓和的因素越多,或者更准确地说,行动的动机就越弱,行动就变得越消极被动,行动就越少,就越不需要指导原则。这样,所有的军事艺术就只能是小心谨慎,它的主要任务就在于使动荡不定的均势不会突然产生对自己不利的变化,使半真半假的战争不致成为真正的战争。
二、战争是政治的一种工具
到目前为止,我们总是在战争的性质与个人和社会团体的利益相互对立的状况下进行研究的,我们有时从这一方面,有时又从另一方面进行研究,以免忽略了这两个对立着的双方的任何一个。这种对立的根源是由于人的本身,因此,进行哲学的考虑是不能解决的。现在,我们力图找出这些矛盾着的方面在实际生活中由于部分地相互抵销而结成的统一体。假如没有必要确切地指出这些矛盾和分别考察每个不同的因素,我们本来在最初就能够谈这种统一体。这种统一体是怎样的一个概念呢?战争只不过是政治交往的一部分,而决不是什么独立的东西。
当然,人们都知道,战争只是由政府与政府、人民与人民之间的政治交往而引发的。但是,人们一般都作这样的想象:好象战争一爆发,政治交往就宣告中断,就会出现一种只受本身规律支配的根本不同的现象。
与此相反,我们却感到,战争就是政治交往用另外一种手段的继续。我们之所以讲是用另外一种手段,就是为了要同时指出,这种政治交往并不会因为战争的爆发而中断,也不会因为战争而变成某种根本不相同的东西,无论利用什么样的手段,政治交往实质上总是不间断地存在的;而且,战争事件所遵守并受其约束的主要路线,只能是贯穿全部战争直到媾和为止的政治交往的轮廓。难道还能够有什么其他的设想吗?难道随着外交文书的中断,人民之间和政府之间的政治关系也就中断了吗?难道战争不正是它们表达思想的另一种文字和语言吗?当然,战争有它本身的语法,但是战争并没有它自己的逻辑。
因此,决不可以让战争离开政治交往。假如离开政治交往来观察战争,那么,就会割断形成关系的所有线索,而且只会得到一种没有任何意义和没有任何目的的东西。
甚至当战争彻底是的战争,完全是敌对感情这个要素的不受约束的发泄时,也应该这样看问题。作为战争的基础的和决定战争的主要方向的所有那些因素,正象我们在第一篇第一章中所指出的:自己的力量、敌人的力量、双方的同盟者、双方的人民和政府的特点等,不是都具有政治的性质吗?不是都和全部政治交往密切结合而不可分割的吗?同时,现实战争并不象战争的概念所规定的那样是一种趋向极端的努力,而是一种自身有矛盾的不彻底的东西;这样的战争是不会服从它本身的规律的,必须把它当作是另一个整体的一部分,而这个整体就是政治;假如我们再想到这些,那么就更需要象上面那样来认识问题了。
政治在使用战争时,总是不考虑那些产生于战争性质的严谨的结论的,它较少想到最终的可能性,而只是用最直接的概然性作为根据。假如全部行动因而出现了很多的不确实性,以致变成了一种赌博,那么,每个政府的政治就都想在这场赌博中,用机智和锐敏的眼力战胜敌人。
这样一来,政治就把战争这个毁灭一切的要素变成了一种单一的工具,把需要用双手和全身气力才能举起作致命一击的可怕的战刀,变成一把轻便的剑,有时甚至变成比赛用的剑,政治用这把剑能够交替地进行冲刺,虚刺和防刺。
这样一来,战争使本性胆小的人所存在的矛盾就自行解决了,假如这可以当作是一种解决的方法的话。
既然战争隶属于政治,那么,战争自然就会带有政治所具有的特性。政治越是宏伟而有力,战争也就越宏伟而有力,甚至可以达到其绝对形态的高度。
因此,当我们这样看待战争时,不但没有必要忽视这种具有绝对形态的战争,而且相反地还需要常常地考虑到它。
只有根据这样的看法,战争才会又成为一个统一体,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一切的战争当作是同一类的事物,而且只有这样,在考虑问题时才能有一个准确而适当的立足点和观点,而这种立足点和观点是我们制订和评价大的计划时需要依据的。
当然,政治因素并不能深入地渗透到战争的每一个细节部分,配置骑哨和派遣巡逻哨,是不需要把政治作为考虑的依据的。但是,政治因素对制订全部战争计划和战局计划,甚至往往对制订会战计划,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因此,在一开始我们就没有急于提出这个观点。在考虑个别问题时,这个观点对我们不但用处不大,反而会在不同程度上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但是在制订战争计划和战局计划时,它却是不可缺少的。
通常地说,在生活中最重要的要算是正确地找出理解和判断事物所应该根据的观点并坚持这一观点,因为只有从一个观点出发,我们才能对许多的现象具有统一的理解,而且也只有观点的一致,我们才不会围困在矛盾之中。
因此,既然制订战争计划时不能有两个或更多的视察事物的观点,例如一会根据军人的观点,一会根据行政长官的观点,一会又根据政治家的观点等等: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其他一切都必须服从的是否就都是政治呢?
我们思考问题的前提是:政治在它自身中集中和协调内政的所有利益,也集中和协调个人的所有利益和哲学研究所能提出的所有其他利益;因为政治本身不是别的,它不过是这一切利益的代表(对其他国家而言)。至于政治有时会出现错误的方向,会主要地为统治者的野心、私利和虚荣服务,这不是现在所要探讨的问题,因为军事艺术在一切情况下都不能够作为政治的导师。在这里我们只能把政治当作是全社会的所有利益的代表。
因此,现在的问题只是:在制订战争计划时,是政治观点应该让位于纯粹的军事观点(假如这种观点是可以想象的话),即政治观点完全消亡或隶属于纯粹的军事观点,还是政治观点仍然起主导作用,而军事观点应该服从于它。
只有在战争是单一因为敌对感情引发的你死我活的斗争的情况下,才能够假设政治观点会随着战争的爆发而消失。然而,正象我们上面说过的那样,现实战争就是政治本身的最高表现形式。使政治观点隶属于军事观点,那是非常可笑的,因为战争是由政治产生的。政治是头脑,战争只不过是工具,不可能是相反的。因此,只能是军事观点隶属于政治观点。
让我们思考一下现实战争的性质,回忆一下在本篇第三章中已经讲过的有关战争的问题。首先我们应该依据因为政治因素和政治关系而形成的战争的特点以及主要轮廓的概然性来了解每次战争,而且经常——在今天,我们甚至能够说在大多数情形下——都应该把战争当作是一个同各个部分不可分离的有机的整体,也就是说,每个部分的活动都应该集中到整体中去,并从整体这个概念出发。这样,我们就会真正确信和明白,并借此来认定战争的主要路线以及指挥战争的最高观点不能是别的什么观点,它只能是政治观点。
从这一观点出发,制订的战争计划就好象是一个铸件一样的完整,对它的认识及其评价就比较容易和合乎情理,它也就显得更有说服力,它所根据的理由就显的更加充分,对历史的了解也就更加容易了。
从这一观点出发,政治利益和军事利益相互间的对立就至少不再是由事物的性质所决定的,因此,假如发生了这种冲突,也只能承认是因为人的认识能力的欠缺而引起的缘故。假如政治向战争提出战争不能够做到的要求,那么战争就违背了政治应该了解它并想把它当作工具而使用的这一前提,也就是违背了一个必须有而又不可缺少的前提。假如政治能够正确地判定战争事件的进展过程,那么,决定什么样的战争事件和战争事件应该向着什么样的方向是与战争目标相适应的,这全都是而且只能是政治的事情。
总而言之,军事艺术在它最高的范围内就变成了政治,当然这不是写外交文书的政治,而是打仗的政治。
依据这一观点,对一个大规模的战争事件或它的计划进行纯军事的评论是不能允许的,甚至是有害的。在制订战争计划时向军人询问,象有些政府经常做的那样,让他们从纯军事观点出发来进行判断,那的确是荒谬的。而有些理论家希望把现有的战争手段交给统帅,要统帅依据手段来制订一个纯军事的作战计划或战局计划,那就更荒谬了。一般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尽管现在的军事是很复杂的,并且有了很大的进展,战争的主要框架始终依然是由政府来决定的,用专业的术语来说,只是由政治当局决定,而不是由军事当局所能决定的。
这全都是事物的性质决定的。假如对政治关系没有深入的了解,是不可能制订出战争所需要的主要计划的。在人们说政治对作战的不利影响时(人们是经常是这样说的),他们所说的实际上根本不是他们心里想要说的意思,他们批评的实际上并不是政治对作战的影响,而是政治本身。假如政治是对的,也就是说,如果政治与它的目标是一致的,那么,政治就它的本意来说就只能对战争产生有利的作用。当这种作用和目标不一致时,那么只能到政治的错误中去寻找其原因。
只有当政治期盼着从一些战争方式和措施中得到与它们的性质不相一致因而不可能得到的效果时,政治才会通过它的决定对战争产生不利的影响。正如一个人用不特别熟练的语言有时是不能够确切地表达出正确的思想一样,政治也往往会作出和自己本来意图不相符的决定。
这种情况连续不断地发生,于是人们就认识到在进行政治交往时应该对军事情况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然而,我们在继续阐述问题之前,一定要防止一种非常容易产生的错误的理解。我们决不以为,在君主本人没有亲自掌握内阁时,一个埋头于公文的国防大臣,或者是一个学识渊博的军事工程师,或者甚至一个能征善战的军人就因此能够成为一名杰出的首相。换句话说,我们决不以为,了解军事是首相的主要条件。伟大而出众的头脑、坚强的性格,这些才是他的主要的条件。至于军事知识,那是能够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很好地给予弥补的。法国的军事活动和政治活动再也没有象在贝利耳兄弟和舒瓦瑟耳公爵当权时那样糟透了,尽管这三个人都是优秀的军人。
要使每一次战争全部与政治意图相一致,而政治又全部和战争方式相一致,假如没有一个既是政治家又是军人的统帅,那么就只有一个好办法,只好使最高统帅成为内阁的成员,以便内阁能参与统帅的主要活动。但是,只有当内阁也就是政府就在战场附近,从而不需要花费许多的时间就能够确定各种事情时,这才是可能的。
一八零九年奥地利皇帝这样做了,一八一三、一八一四和一八一五年反法联盟各国的君主这样做了,而且这种做法说明这是完全行之有效的。
在内阁中,除了最高统帅的权威外,任何其他军人的权威都是非常危险的,这种权威极少能够引导出健康而有力的行动。法国的卡诺于1793、1794和1795年从巴黎指挥作战的例子在这里是用不上的,因为只有革命政府方会执行可怕的政策。
现在我们想用历史的考察来结束本章。
上一世纪九十年代,在欧洲的军事艺术中出现了一种震惊天地的变革,由于这种变革的出现,那些出色军队的战术技巧有一部分已失去了作用,同时,人们在战争中获得了一些过去很难想象的规模非常之大的成就,于是,人们自然就感到所有错误的计算好象都应该归咎于军事艺术。非常明显,军事艺术以前一直被常规地局限在这个观念的狭窄的范围里,现在,超出这个范围但又符合事物性质的可能性使它觉得意想不到而不知所措了。
那些以开阔的视界考察事物的人,把这种情形归咎于几世纪以来政治对军事艺术所产生的十分不利的普遍影响,这种影响使军事艺术降为一种不完全的东西,时常降作一种完全的耍花招的艺术。事实确实是这样,然而,只把这种情形当作是突然产生的和能够避免的,那的确是错误的。
另外一些人感到,这一切都能够从奥地利、普鲁士,英国等个别国家的政治所发挥的暂时影响中得到解释。
然而,人的智力觉得意外而不知所措的原因果真是在军事范围内而不在政治本身吗?用我们的语言来说,这种不幸究竟是出于政治对战争的影响呢,还是出于错误的政治本身呢?
显然,法国革命对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与其说是因为作战的新手段和新观点引起的,不如说是由于完全改变了的国策和内政、政府的特点和人民的状况等引起的。至于其他的公国政府不能正确地理解这一切,妄图用惯用的手法和同那些新的和压倒一切的力量相抵抗,这都是政治的错误。
那么,人们以纯军事的观点来对待战争是否能了解和改正上述错误呢?不可能。假如真的有一位有哲学头脑的战略家,他可能只依据敌对条件的性质就推出所有的结果,并想依据这一结果对将来的可能性作出预言,那么他的这种妄想是根本不会得到任何结果的。
只有当政治能够正确地预计法国的觉醒力量和欧洲政治中新出现的关系时,政治才能预见到战争的大的框架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是什么样的,而且只有这样,它才能肯定必需使用的方法的规模和选择使用方法的最好的途径。
因此,我们可以说,法国革命所得到的二十年胜利,主要是各国政府反对这次革命而引起的政治错误。
当然,这些错误只是在战争当中才显露出来,在战争中出现了与政治所抱有的期望完全相违背的现象。所以出现这种情形,并不是因为政治没有向军事艺术请教。政治家当时所信任的军事艺术,是他那个世界的军事艺术,是隶属于当时的政治的军事艺术,是政治一直当作十分熟悉的工具来使用的军事艺术,这样的军事艺术,我们认为自然和政治有一样的错误,因此它不能改正政治的错误。的确,战争自身在本质上和形式上也产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使战争已经更靠近其绝对形态,但是,这些变化并不是因为法国政府已经脱离了政治的羁绊而产生的,而是因为法国革命在法国和全欧洲引起了政治的变化而产生的。变革后的政治提供了不同的方法与和不同的力量,因而使战争产生了在其他情形下很难想象的威力。
因此,就连军事艺术的实际变革也是政治改变的产物,这些变革不但不能说明两者是能够分割的,反而有力地说明了两者是密切结合的。
我们再重复一遍:战争是政治的工具;战争不可避免地具有政治的特性,它应该用政治的标尺来进行衡量。因此,战争就其主要方面来说就是政治本身,政治在这里以剑代笔,但并不就是说不再遵照自行的规律进行思考了。


 微信登录
微信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