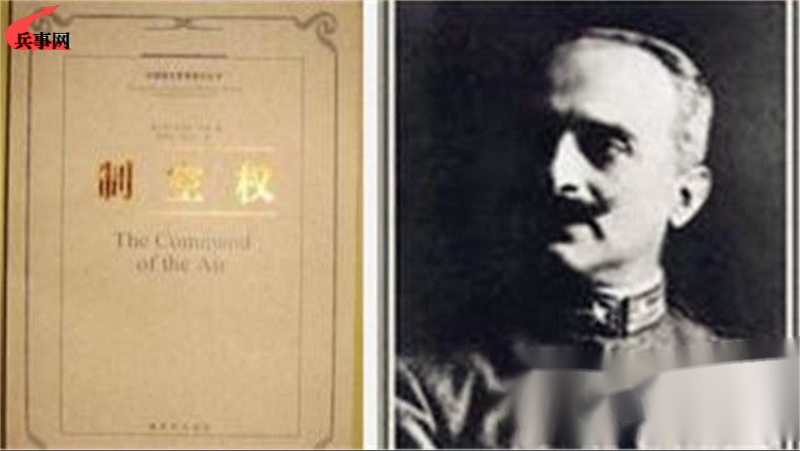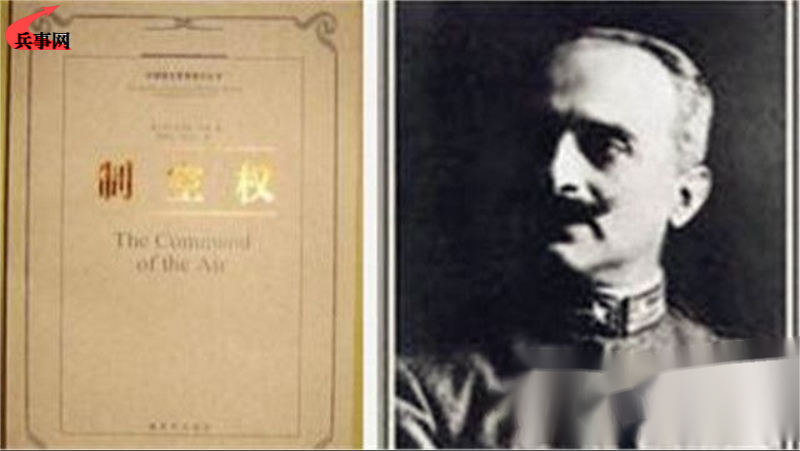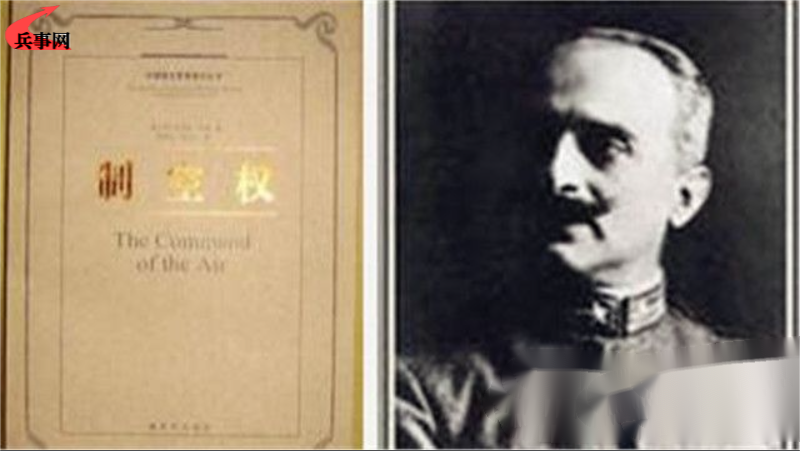未来战争的可能面貌·第一
出自————《制空权》《第二部·未来战争的可能面貌》
出自————《西方军事著作》
在这一章中我们将简要考察这次世界大战,探讨它的主要特征。这是我们经历过的事件,是我们获胜的战争,作为协约国获胜,作为意大利人三次获胜:第一次是脱离三国联盟,使法国在马恩之战 [ 译者注:指1914年8-9月德法在巴黎附近马恩河地区的会战,双方死伤达50万人,德军战败。 ] 中获胜;第二次是在协约国的关键时刻参战;第三次是和协约国一起走向胜利。这就是我们值得骄傲地回忆的事件,这个回忆使我们心情激动。但是,如果我们想为通向未来的旅程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我们应当暂时忘掉上次胜利精神上的优美和道义上的伟大,而应当冷静地考察它,正如一名外科医生冷静地解剖一具尸体,探索生命的奥秘,而并不使自己为这一度存在的生命而伤感。
世界大战是一个巨大的悲剧,整个世界成为剧场,人类成为其中的角色。要想追溯它的过程,我们应当站得更高来观察,把望远镜反过来看,用钟表的短针计算时间,按月而不是按小时计算。如果我们这样做,就能立刻看到世界大战具有一种和以往任何战争不同的特性,我称它为社会性。以往的战争是程度不同的专门化军队之间或大或小的冲突。当时这是作为一种“最终方案”,各国按照惯例,使用为此目的而专门组织的特殊集团 [ 原作者注:过去叫职业军队,通常是雇佣兵。 ] ,解决它们之间的冲突。这些集团在陆上和海上交战,其结局由有关国家自愿接受。几千人之间的交战常常足以决定整个民族长时期的命运。
各国首脑通常从人民中为自己的军队收集物资,用它进行战争这场大赌博,赌注常常就是人民本身的命运。军事搏斗的输赢决定了事情的结局,除非引进新的军队重新开始搏斗。只有军队决定这类冲突的结局,它在整个人民中只占一小部分,有时是很小一部分。大部分人民置身事外,即使不是对整个事情漠不关心,也几乎是不加注意。简而言之,这些国家首脑是在用称为陆军和海军的特殊棋子在战争区这个棋盘上走动,为自己的命运和本国人民的命运在对奕。因此,冲突的结局取决于棋子的数量和质量以及棋手的能力。“军事学”,也就是最佳棋法的汇编,它包括一系列下棋规则和要求;棋子布局即编制;棋子走动即战略和后勤;出击是战术,能够比较出色地运用这些规则和要求的人即成了伟大的将领。
棋局的主要规则(基础的、直观的,所谓基本原则)保持不变,因为尽管棋子形式有变化,而棋手始终相同,棋局始终一样。但即使主要原则不变,它们在具体情况下的运用则取决于棋手。伟大的将领只不过是较聪明、幸运的棋手,即使自己的实力小于对方也能取胜。他们实质上是一些能摆脱传统、能使老旧的棋术获得新生的棋手。事实上,伟大的将领就是一些具有伟大博奕者心理的人。他们相信自己的运气,关键时刻大胆行事,对敌人的手法有本能的了解,有欺诈能力,能掌握计谋和突然性艺术,绝对相信自己的最后一张牌。
这就能解释历史上看似荒谬的事件。例如,它能解释为什么拿破仑仅以一小群人就横扫欧洲。但是,尤其在世界大战前夕,人民开始认识自己的力量,几乎不知不觉地感到,把自己的命运寄托于只占自己全部力量一部分的人的战斗结局是荒唐的。当两个人或两个动物进行生死搏斗时,他们投入自己的全部力量去斗争。他们的唯一目标是取得胜利。一旦各国人民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各国之间的斗争也必然出现同样情况。他们必将用全部能力和资源投入斗争。对于一个将死的人,一切节省都是无用的。
普遍征兵扩大了武装部队的规模,但这还不够,人民还掌握着其他巨大资源,而所有这些也必须参加斗争。因此世界大战必然具有两个民族联盟之间以其全部能力、全部资源、全部信念进行的巨大生死斗争的特点。
因此,在世界大战中,棋局中的棋子是使用其全部精神和物质财富的人民本身。武装部队只是参加斗争的人民力量的一部分。以往战争中,武装部队是进行斗争的唯一力量,而世界大战中的力量则是人民自己,武装部队仅仅是供他们使用的手段,只要人民保持坚定,也就能坚定地掌握它。但是当人民开始屈服,一支仍然强大和有纪律的陆军也就会屈服,整个舰队也就会完整地投降敌人,如象德国的情况那样。
这样一种战争的结局不能依据某些聪明的将领在棋盘上走动棋子来决定,不能由单纯一件军事事件或一系列军事事件来决定。大群高度文明的人民,成百万有觉悟的人,是不会把他们的未来托付别人,也不会把他们的命运寄托于一个“佣兵首领”的某种突击或某个武装集团的英雄主义上。两个国家集群必然要直接进入冲突,不顾一切地投入交战旋涡。任何一方除非全面崩溃,就不会退却或承认失败。这种崩溃只有通过精神和物质上严重、持久、复杂的解体过程才能发生,这个过程几乎不受战争的纯军事活动的影响。
这就说明为什么赢得最多军事胜利的一方反倒成了战败的一方。这就说明了战争为什么持久,因为需要打败一群国家,而不仅是一群军队。这也就解释了战胜国和战败国双方战后所处的状况。
当战争仅仅由武装部队,即只由国家人力物力的一小部分所决定时,没有参加斗争的人力物力,无论战胜国或战败国,都能不受触动。战争的影响很难被人民感受到。只不过是战胜国从战败国索取赔偿,重新开始新的斗争。但是这次世界大战却耗尽了所有参战民族的资源,一方的全部力量在另一方全部力量压迫下完全瓦解。胜者精疲力竭,败者被剥夺了一切。战败国犹如遭受风暴袭击一样被破坏,而战胜国也由于付出极大的努力而衰竭,并且发现不能从被它战败的敌人身上补偿自己的损失。
我们用倒过来的望远镜观察,能够理解这次战争的社会性,认识到它的后果。能够首先认识到现存原因会导致不可避免的结果,这是有益的,其实首先认识到这一点并不难。为了证明,让我引用1914年八8月11日都灵《人民报》上一篇文章的几段话,标题是:“谁能胜利?”
今天要说这场巨大战争的结局如何似乎是大胆的,但并非如此。这场巨大斗争的各种因素在大的方面是清楚的,因为它是由参战国全部物质和精神力量所构成的。今天各国不再把它们的命运托付给一支军队,军队一旦被打败,国家也就战败了。今天的斗争范围更大更复杂,这是国家之间而不是军队之间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战场上一次胜利或多次胜利并不足以决定结局,更重要的是国家的抵抗能力。
如果我们根据军队的实力和部署、它们的可能行动、参谋部的各种准备来进行预测,我们将犯大错误,因为我们忽视了真正的对抗力量——国家本身,军队只不过是斗争中的代表。不是法、俄军队对抗德、奥军队,而是法国、俄国、英国对抗奥地利和德国。这个差别是很大的。
在这样一场巨大的斗争中,德奥军队想要通过内线作战取胜,是注定要失败的梦想。中欧强国 [ 译者注:指德、奥两国。 ] 迟早必然会发现它们面对着整个法国、整个俄国、整个英国。胜利将属于懂得在战斗中如何更有利地运用兵器、力量、信念进行抵抗的一方。德国和奥地利的海港被封锁,陆地边界被为生存而战的敌国所包围,正如被一个铁环锁住。它们像一对野猪被一群猎犬紧逼在洞穴里,左奔右突,这边冲开了,那边又收紧,而猎犬的威胁越来越凶猛,直到野猪力尽被咬死,森林中响彻负伤猎犬准备庆贺的胜利吠声。
这篇写于世界大战第一周的文章是一个战争预测。看来预见战争的主要特性并不难。但是不然,有关各国政府并未能看到即将发生的战争必然具有的特性。
今天,人们几乎不能相信,像德国参谋部中那些无疑是有教养有智慧的人仅仅由于完成了一次出色的军事机动就坚信“德意志高于一切”,更不能相信军界以外的治理德国的人也接受了同样的思想。可是事情正是这样。
这种怪事所以能发生是因为其他怪事早巳存在。事实上,尽管战争逐渐趋向总体化(即战争吸引前所未有的众多的平民参加),可是政权和军权的分界却越来越明显。当政府首脑统治人民时,这两种权是重合的,而当政府转为民意代表时,政权与军权之间就产生了矛盾。按照自然演变,战争越是需要平民参加,平民就越是把有关战争的事务委托给一批专门人员,绝对信任地将军事问题托付给他们。在民事与军事之间建起了一堵墙,切断了它们之间的一切联系,隔绝了彼此的了解。墙内的人从事的工作在普通人眼里似乎是神秘的,觉得难以理解,甚至几乎带着崇敬的心情看待它。
在那个圈子里作出的任何决断都被人们无可争辩地加以接受。当危机爆发时,国家命运即完全交给这些名义上胜任的人去支配,而他们却一直脱离国家的生活、工作和活动。一旦宣战,政治当局停止活动,把进行战争的任务委托给军事当局,政治家们则袖手旁观。军事当局方面力图限制政治活动而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政府按其性质不胜任军事事务,却有权任命和免除最高指挥官。这种任命和免职表示一种判断,而这种判断却是由对战争责任不胜任的人作出的。显然,国家必将为这种职责上的怪事付出代价。
许多国家仍然存在着这种情况。在意大利,国家元首的智慧结束了这种状况。政府首脑也就是武装部队首脑,对战争准备有最高控制权,必要时,也将拥有进行战争的最高指导权。
这种对于战争特性的不了解,其最主要的后果在战争本身表现了出来。德国总参谋部由于只考虑军事方面,相信它的作战计划和它的部队准备都是出色的,从而断定将迅速取得决定性胜利并且代价较低。但是这种判断是建立在对形势的错误估计之上的,而政治家们不加仔细考察也就接受了,认为它是由职责上胜任的机构——总参谋部作出的。如果治理德国的那些精明的人不被总参谋部享有的崇高声誉所迷惑,如果他们考察一下有关问题的实际情况,他们就很可能对形势有比较清楚的认识,看到不可能取胜以及斗争要付出惊人代价。他们对这场赌博就可能会裹足不前。
陆上的战争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是从战争开始到马恩之战,第二是从逐步建立绵亘的战线直到战争结束。第一时期和第二时期相比很短,是一个调整时期,从表面看,具有和以前的战争几乎相似的面貌。我说“几乎相似”,因为它是一场运动战;我说“从表面看”,因为它所进行的各次交战不是决定性的,只是导致形成绵亘的战线,成为整个这次世界大战的最主要形式。
从经典的观点看,德国的战争计划在战略上是无懈可击的。它使人想起了拿破仑,是建立在著名的内线机动之上的。它把自己摆在中心位置,利用自己的优势,能够依次打击四周的一个或数个敌人。当然,它为了成功,必须在其他敌人围上来以前决定性地击败其中一个,否则将陷入重围。对德国人来说,他们必须在俄国人全力投入战争之前先击败法国陆军。因此,他们以其强大的、组织良好的军队,对法国人发动了一场快速的坚决的进攻。为了速决,他们避免正面攻击而转向法军左翼。这就必须通过比利时。他们也并不犹豫,因为战略要求必须如此。他们知道侵犯比利时会使英国参战,但他们指望英国陆军没有做好准备。通过法军左翼迅速进抵巴黎,由此获得的战略利益被认为超过比利时和英国的参战。一旦击败法国陆军,他们就会有充分的时间去打击俄国人以及这时英国人可能动员的任何力量。因此,德军总参谋部并没有充分认清形势,把战争看作是传统战场上的棋局,执行了它的经典计划,不惜使英国以其全部力量投入了对德国的战争。德国政府追随总参谋部之后,宣布条约成为废纸。
建立在相同理论上的法军总参谋部的战争计划也是简单和冒进的,没有考虑敌人的计划及其兵力规模。很难设想比法国更简单的战略,它可以归纳为几个字:“前进,相信胜利!”在实证主义的十九世纪,就没有人会把国家的安全寄托在这样一种天真的理论之上了。但是法军总参谋部肯定是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的,却固步自封,脱离现实生活,受一种近乎神秘的信仰的影响,一直到在事实的无情冲击下遭到失败为止,信奉和企图执行的正是这样一种天真的计划。
事实上,从比利时到瑞士的整个边界上都部署了法国军队。在中部后方有一支预备队,受命在敌人进行任何机动时突击它并压倒它。法军在部署就绪之后,打算以全部力量从两翼同时发动进攻。法军总参谋部无疑知道德国企图突击它的左翼,但它对这种可能的危险考虑不够。一旦德军通过比利时,法军就打算将自己的左翼向西北延伸。如此而已。
战争一开始,法军的进攻能力在最初几次无关大局的交战中就消耗掉了。德军右翼压倒了对抗的劣势法军。9月2日,法军总参谋部下令后撤100公里,米尔朗 [ 译者注:亚历山大·米尔朗,当时任法国陆军部长。 ] 甚至要求部长会议宣布巴黎为不设防城市。但上帝并不打算过于严厉惩罚法兰西。发生了马恩之战,随之双方向海峡港口前进,建立了一条绵亘的战线。
从这时开始,战争基本具有了相持的特性,直到终结。从这时起才真正是国家之间的冲突,一切与以往战争相似之外,一切过去的传统战争活动,都消失了。
在被不可逾越的天然的或政治的障碍所阻挡而形成的接触线上,挖了战壕,修起了胸墙,构筑了带刺铁丝网;人员、步枪、机枪、大炮沿线分布,开始了赶退敌人的比赛,忽而这边,忽而那边,忽此忽彼。它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战争,更象是绵延数百公里的没完没了的战斗。它沿漫长战线的各个地段进行,忽而激烈,忽而平息。持续了好几年,绵亘战线始终没有真正被突破,因为只要有一段被突破,很快在其前面或后面就会连接起来。
这是一个相持的战争。它不是一场军队相互交锋的战争。而是国家相互围困的战争。它象两个摔跤手,没有抓住对手摔倒在地,而是肩对肩地相持着,各自等待着对方由于肌肉和神经的持续紧张而导致精神崩溃。这是一种没有先例的斗争,面貌全新,它使一切传统的经典战争规则全部失效。
机动是不可能的,因为你不能对着中国的长城机动。战略也投有用了,因为战略是在战场上展开人群的艺术,而在这场战争中各群人已经固定地展开,彼此面面相对。战术这种选择各自攻防地域的艺术也没有用了,因为在这场战争中没有了地域选择;这里只有一个战场,没有人能改变它。军事学术已不再起作用,因为不能再投入潜在力量,全部物质力量都已经用上了。这是一场无休止地进行最野蛮的屠杀的战争;这纯粹是一场尽力杀伤和破坏的残酷战争。
出现一条绵亘的战线对每个人都是意外。它直接违反一切现行理论和所有参谋部的思想习惯。历史上有过一些防御作战的战例,守方试图建立一条坚固的防线,但是攻方总是能集中力量,很容易地突破它。如果攻方面对敌人的坚固防线而也要沿一条固定战线展开自己的兵力,这种思想被认为是荒唐的,世界所有军事学院的学究们可能都会这样说。可是现在,以往的事都过去了。两条战线彼此相对,只能相互敲打。
还出现了更奇怪的事。一些国家新加入战争,它们的军队也立即占据了同样的绵亘战线,而且常常是沿着最长的战线展开。我们自己在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也将我们的军队沿着斯太尔维奥到海边的不间断战线展开,我们发现面对着我们的奥地利人也据守着从海边到斯太尔维奥的不间断战线。没有一家总参谋部预见到这样一种战争形式。他们都感到意外并试图作出反应,但是无用,因为这种绵亘战线是无情的、有威力的、不可改变的现实。
这一奇特的、普遍出现的现象原因是什么?违背指导这场战争的人们的意志而出现的这种现象,肯定是由某种普遍性的、到处存在的,不能单由人的意志改变的原因造成的。
这个原因纯粹、完全在于火器,尤其是小口径火器的巨大效力。理由是火器、尤其是小口径火器效力的任何增强,都增大了防御的作用。如果我处在一个堑壕中,有一支一分钟射击一发的枪,我至多只能阻止一个由一分钟距离外向我跑来的进攻者。如果两名敌人同时向我攻击,我能阻止一个面不能阻止另一个。但是如果我的抢每分钟射击一百发,我能阻止一百名由一分钟距离外向我跑来的进攻者。因此,我的进攻者应当有一百零一人,以便其中至少有一人能到达我处。按第一种情况,我在防御时能对付一个进攻者,而按第二种情况我能对付一百个。这时除了我的枪的效力外,其他并没有改变。
如果在这两种情况中,我都在战场上布设足够的铁丝网障碍,使进攻者速度减慢到需要五分钟才能通过战场,那么按第一种情况我能阻止五个进攻者,按第二种情况我能阻止五百个。除了枪的效力,其他并没有改变,但是由于铁丝网障碍,间接改变了这个效力的大小。在第一种情况中,我能比没有铁丝网障碍时多对付四名进攻者,在第二种情况中多对付四百名。
这些,用于保护自己部队的手段——堑壕和用于在堑壕前面迟缓敌人前进的手段——带刺铁丝网和其他类似设施,对防御体系有很大的重要性,因为它们使较小的兵力有可能对付大得多的兵力。因此,火器的一切改进都有利于防御,使进攻付出更重的代价,使进攻必须以优势的兵力进行。
实际上,防御作用的增大是立即可见和十分清楚的。最强大的进攻也很容易被较小的挖有堑壕的部队(即使是临时设置的堑壕和障碍)所阻止。这就导致战线的凝固。因为双方一旦接触,谁也不能突破,只有停止,挖壕固守。在马恩之战和冲向海峡港口之后,双方战线逐段凝固直达北海。防御所起的作用使战线兵力减少,从瑞士连绵不断地一直延伸到海边,因为由于防御的优势,即使兵力减少,仍然难以突破。
如果使用的还是老式的前膛枪,就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现在双方每个人都有速射火器,不可能使他们再回到过去使用前膛枪时那种进行战争的传统方法。
没有人预见到这种情况,也许德国人除外。相反,另一种信念到处流行,就是认为火器的改进将有利于进攻。这种见解公开发表在当时的官方文献和教范中。为什么犯下了这种技术错误、这种必然带来了严重后果的错误呢?很难说为什么,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它一定不是某一个人的主张。人们曾经充分地研究了一八七零年的战争 [ 译者注:指一八七零年普鲁士和法国军队在亚眠地区的战争。 ] ,从中汲取教训——从以往战争中汲取教训已经成为传统的作法。一八七零年德国人一直处于进攻,他们总是胜利。由此就引伸出:他们总是胜利因为他们总是进攻,而忽视了这个事实,即他们总能进攻是因为他们较强。人们甚至进一步宣称进攻是致胜的万应良药。因此,军方的思想完全转向了进攻,总是不惜代价地进攻。在法国当时有一种很流行的思想,主张指挥官应当集中一切力量用于进攻,甚至发展到可以不考虑搜集有关敌人情报的地步。
在和平时期的演习中,进攻一方总是成功的,因为没有一个裁判敢于想使防御一方得分。至于防御虽然从来不是决定性的,却能帮助争取时间和集聚力量——这种思想完全被置之不理,甚至发展到有的军队在他们的战术教令中都不提防御这个词。也就难怪在这种思想习惯支配下,人们不可能认识火器效力的增强对防御要比对进攻更有价值。相反,人们把火器效力的增大看作是进攻能力的增强,这可能是认为每分钟射击一百发的枪要比只射击一发的枪能打更多的人。
绵亘战线自发地和意外地出现,防御显示出惊人的效力,通常的战争规则的失效,这些引起了严重的迷惑。最勇敢的、训练最好的、士气最旺的部队被步枪机枪的速射火力阻止在带刺铁丝网前面。反复攻击,结果总是一样。它以进攻者的精疲力竭而结束,防御者守住了阵地或后退,斗争停息,等待重新开始。来自孚日的代表阿贝尔·费里,参战时是步兵中尉,国务次官,陆军委员会成员,一九一八年九月二十五日死在战场上。在战争爆发之后二十二个月,他写道:
只有参加过这次战争的人能够认识到,法国总参谋部对于战争性质、机枪火力、带刺铁丝网的价值、重炮的必要性是多么无知。我们的总参谋部具有很高的道义感和伟大的个人品质,非常努力进行战争准备,但不幸是沿着错误的方向。我们总参谋部的军官使自己成为拿破仑战争的专家,但是忽视了经济、工业和政治力量;他们不是现代国家战争的专家。没有预见到和研究过主要由小部队进行的堑壕战。总参谋部对它完全不了解,他们没有经历过它,也没有领导过它。这种经验还没有由基层传到上层。
当一切战略计划都已经失败,当一堵墙对着另一堵墙建立起来时,斗争变得分散而不协调。由于即使付出沉重牺牲也不能取得战略成果,交战的军队不得不退而争取战术成果,但是这些战术成果的代价也是很大的。它们开始占有重要地位。既然在任何地方付出代价就能取得战术成果,战术活动也就成了整个战场的特点。在有利的季节,在调进足够数量的人员和弹药以后,也会周期性地进行一些大规模活动,在人员和物资上都付出了很大代价,而结果至多只能是部分地楔入敌人防线。在一系列这种行动之后,战线变得扭曲奇特,不是出于任何战略战术考虑,而是双方在各地进行无效的进攻遭到阻止的结果。偶尔在战线上造成一个较深的突破,又总能设法重新建立战线。实际上,尽管经常进行代价很高的行动(可能比以往任何战争的代价都要高),每次也只能是插曲式的单个战役,从马恩之战延续到最终胜利,一直如此。
进攻永远比防御代价大,直到它能压倒防御。进攻一方在胜利后将大量收获自己劳动的成果。但是进攻一方在达到目的以前如果被阻止,那就纯粹是损失,因为进攻者的消耗要比防御者大。这个事实不是看不到的。但是为了替进攻辩护,产生了法国的啃食 [ 原作者注:象老鼠那样啃咬东西。 ] 理论。
这种理论建基于这样的前提,即协约国比中欧强国具有很大的人数优势,即使每次进攻确实使我们付出比敌人更大的代价,但是既然敌人的人力比我们少,即使在这期间我们会遭受比它更大的损失,最终我们将把它拼垮。这个理论违反了军事科学,严重妨害了取得最终胜利。因为在俄国崩溃以后,协约国已不再享有人数上的优势,他们遭受的巨大损失已经对西线协约国军队产生了瓦解士气的效果。
一九一六年七月阿贝尔·费里就沃厄弗战役情况送给了维维阿尼内阁成员一份备忘录,他写道:
消耗战不仅是公开承认战略上无能为力,还将导致未来法国的破坏,这是一种新闻界的方案,而不是军事方案;不管怎么说,这种战争是危害我们本身的战争。当我三月十八日回到团里的时侯,它正因愚蠢的英雄事迹而兴奋。我的连有二百六十人参加攻击,只有二十九人返回。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第八连。在得而复失的德国堑壕里,只找到了一个被打死的德国人。二十七日我们再次攻击,又一次被挡住了。四月五日、六日,十二日,我们又发起了攻击。特里翁炮台的光荣守卫者X上尉甚至单独跑出了战壕被打死了。这个勇敢的团现在已经丧失了它的一切进攻能力,最多只能呆在堑壕里了。我可以说我所知道的其他二十个团也都如此。
他们说,由于准备不足,对敌人采用人海战术能提高我们的士气。但是躺在德国堑壕前面的成千死去的法国人,相反却提高了我们敌人的士气。如果继续这种人力的浪费,那么不要很久,我军已经严重削弱的进攻能力将会完全被破坏。
对于进行那些大的进攻,一切牺牲都是值得的,而这些小的局部攻击只适用于发布每天的战报,却已经造成三十万至四十万人的无谓牺牲。去年十二月仅仅对哈特曼·威勒堡的攻击就损失了我们一万五千人而没有夺得一米堑壕。
一九一七年五月,在著名的尼维尔 [ 译者注:罗贝尔·尼维尔,当时任法军总司令。 ] 进攻中法国人流了许多鲜血,而毫无成就之后,作为陆军委员会报告人的费里这样结束了他的报告:
悲惨的时刻来到了。法国的士气受到了严重损害。一些度假的士兵听到人们高喊:‘和平万岁!’这就是过去三年来我们的军事活动收获的结果。法国政府没能从统帅部没头脑的政策中保全法国土兵的生命。”
这个时刻确实是悲惨的,不仅对法国,而且对整个协约国。接替尼维尔的贝当感到俄国不久将崩溃,采取了一个新方针,避免无益的进攻行动,以拯救生命,提高军队和全国的士气。但英国在一九一七年整个夏季和秋季,发动了一系列攻势,付出了四十万人以上的代价。他们无法补偿这个损失。因此,当一九一七年下半年俄国人签署停战协定后,协约国人力不足,士气低落。只有当美国军队开始进入法国,才重新恢复了平衡。
战争最终阶段的特点是政策和方法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协约军认识到必须节省部队争取时间,等待美国援军到达和得到充分训练。德国人认识到战争必须要在美国以全部实力作后盾的援助起作用之前尽快解决。并且协约军放弃了过去的消耗战理论,认识到最好让敌人去发动进攻直到精疲力竭,然后自己再进行反攻。从那以后,战争的进行导致了胜利。
保持主动并不一定意味着有任意发动进攻的自由,它也可以意味着能自由地让敌人进攻,如果这样更为有利的话。这是协约国在战争开始时就应当采取的合理的、经济的方法,而且如果他们的头脑没有被进攻的神话所迷惑,本来是会这样做的。协约国不仅对于战争没有作好准备,而且也没有充分了解战争的实际。他们本应争取时间来增强和投入他们潜在的实力,造成由于防御作战的作用增大而必需的人力物力优势。他们本应避免一切无用的攻击,因为时间是他们最好的朋友,是对方最坏的敌人。一个人应当永远按照与敌人相反的方案去做,因此他们应当推迟决战,直到拥有一切必要的手段,使之有利于自己。这就是他们一开始本应当做的,而不是象一头公牛那样对着敌人挥舞的红布冲上去。
如果在这个等待阶段中欧强国采取攻势,那就更好,他们将会更快地耗尽自己。不要用到手的人员弹药每隔一段时间就向敌人发动一次没有积极效果的攻击。最好能使自己的防线成为攻不破的,然后在后面集结具有巨大能量的大量部队,以便有朝一日能有效地行动。
这种人力的巨大浪费并不总是值得的,它不仅本身是个错误,而且对协约国也成为一个严重的政治损失,因为他们不得不承认,是美国的帮助使局势转得对他们有利。这导致美国在签订和约中和以后处于控制地位。
对世界大战陆上战争这一概略的回顾,使我们能看出它的最重要特性。这是一场国家之间的斗争,它们以全部实力投入战争,彼此试图用消耗战来拖垮对方。两军在阵地上交战,但由于小口径火器的威力所起的作用使防御的价值大大增加,因而双方都不能从阵地上运动。我们也看到,由于对小口径火器的改进这一技术因素作出了错误的估价,军队在进入战斗时对它所要进行的这种战争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没有准备。事实上,在战争过程中每件事都要起变化,很多东西都要改造。平民的动员进行得很慢。在英国,征兵法令激烈地辩论了很久,而法国总参谋部直到战争发生二十二个月以后的一九一六年五月三十日,才通过了制造速射重炮的计划。由于战前没能回答即将到来的这场战争将是什么样的问题,危及了它的胜利结局,延长了战争,使胜利付出了更大的代价。
这是制度而不是人的错误。按照当时人们所处的活动条件,他们被强烈的爱国心和炽热的信念所鼓舞,已经尽了人力所能做的一切。我们应当衷心地向他们致敬。
战争有它不容忽视的经济方面。战争目的是胜利,但也应当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成果。在这里,代价是人民的鲜血,目的是拯救国家。战争是无所不包的,没有一个人能摆脱它,离开它。罗马在它最光辉的时代曾从它的永久公民中挑选了最优秀的士兵,他们全都热情地关心军事学术。年青的罗马人在开始学习政治、法律、公共行政、哲学、演讲——一句话,在懂得并参加了罗马公共生活之后,即想要进行军事活动以赢得荣誉和声望,然后再回到他们的政治和行政事业中去。凯撒并没有终生从事军事而成了伟大的统帅。他运用了使他在政治上成功的先天能力。他的天才、智慧、明确的直觉、适应能力、坚定的意志,都助成他获得军事声誉。
过去是正确的,今后也仍将正确。国家战时的领袖不能只关心军事,而应当关心本国和其他国家多方面的活动。换言之,他必须是位真正的领袖。
回顾过去,如果我们能看到我们所犯的错误,看到我们应当部份承担的责任,那么我们对赢得的胜利就更能感到骄傲,因为我们不仅战胜了敌人,也必须战胜自己。这就是为什么我这个被称作吹毛求疵的人,却要赞颂那些无名战士,把他们看作我们常胜的伟大民族的神圣象征。


 微信登录
微信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