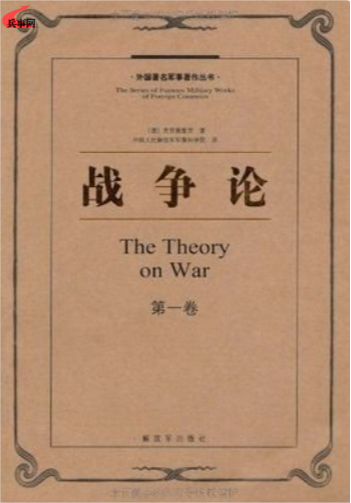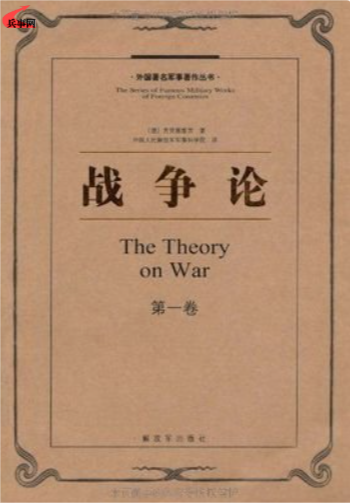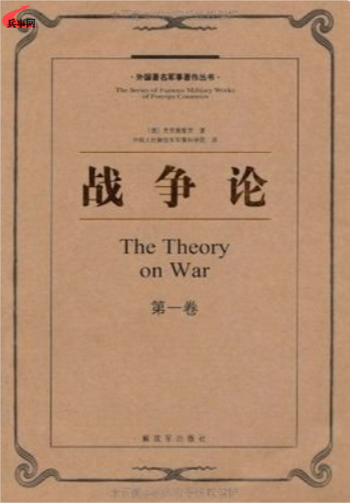抵抗的方式·第八
出自————《战争论》《防御·第六》
出自————《西方军事著作》
防御的概念是抵御,在抵御中包含有等待,等待是防御的主要特征,同时也是防御的主要优点。
但是,战争中的防御不能是单纯的忍受,所以等待也只能是相对的。至于同等待有关系的对象,从空间上讲,是全部国土、战区或者阵地,从时间上讲是战争、战局或者会战。
这些都不是固定不变的单位,只是纵横交错的一定范畴的中心。可是,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往往只满足于只对事物进行分类,而不严格地加以区分,而且这些概念在实际生活中已经十分明确,因此,我们可以根据它们来确立其余的观念。
因此,国土防御只不过是等待敌人进攻国土,战区防御只不过是等待敌人进攻战区,阵地防御只不过是等待敌人进攻阵地。防御者在此后实施的任何积极的、因而或多或少带有进攻性质的活动,都不会改变防御的概念,因为防御的主要特征和主要优点——等待,已经实现了。
从时间范畴来区分的战争、战局和会战同国土、战区和阵地是相应的概念,因此我们上面就国土、战区和阵地论述的问题也适用于战争、战局和会战。
所以,防御是由等待和行动这两个性质不同的部分组成的。当我们使等待同一定的对象发生了关系,并在采取行动之前先进行等待,我们就有可能把两部分结合成一个整体。但是,一次防御行动,特别是一次大的防御行动,如战局或者整个战争,从时间上说,却是由等待和行动这两种状态交错构成的,因此,等待能够象一条长线贯穿于整个防御行动之中。
我们所以这样重视等待,是因为任何理论迄今还没有把等待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提出来,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它已经不自觉地成为行动的根据了。等待是整个军事行动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以致没有等待军事行动几乎就不可能存在了。因此,在以后谈到等待在力量的相互作用中的效果时,我们常常还要提到这一点。
现在我们想谈谈,等待这个因素如何贯穿在整个防御行动之中,以及由此可以产生哪些程度不同的防御方式。
因为在国土防御中,政治关系非常复杂,而且影响也比较大。我们打算把国土防御留到《战争计划》一篇去研究,而另一方面,阵地上和会战中的防御行动是战术问题,它们只有作为一个整体才是战略活动的起点。因此最能说明防御的情况的是战区防御。
如前所述,等待和行动(行动常常是反攻,也就是还击)是组成防御的两个十分重要的部分,没有等待,防御就不成其为防御,没有行动,防御就不成其为战争。因此,防御是可以更有把握地战胜敌人的一种较强的作战形式。我们所以必须绝对坚持这一观念,一方面是因为归根到底只有它能使我们避免犯错误,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一观念越是生动,越是为人们所掌握,就越能使整个防御强而有力。
还击是防御的第二个必要组成部分,如果有人只把狭义的抵御,即把守卫国土、战区和阵地看作是必要的部分(这一部分活动只进行到足以保障这些地区的安全为止),而把转入真正战略进攻的进一步还击却看作是同防御无关的、可有可无的东西,那么,这种看法是同我们上述观念相违背的。我们主张把报复思想作为防御的基础;因为不论防御者最初的还击在顺利时能使敌人受到多大损失,仍然不能造成进攻和防御在对比关系上所需要的均衡。
因此我们说:防御是可以比较容易地取得胜利的较强的作战形式,可是这个胜利是否能超过防御原来的目的,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但是,防御是同等待这个概念分不开的,所以只有在出现了进攻的条件下才能实现战胜敌人这一目的。因此,如果没有出现进攻,防御就只能满足于保持原有的东西,这是防御在等待状态中的目的,也是它最直接的目的。同时,防御只有在满足于这一较低的目的时,才能得到它作为较强的作战形式的那些优点。
假设一支军队奉命防守它的战区,那么防御可能以下列几种方式进行。
(一)敌人一进入战区,军队就立即向他进攻(如莫尔维次会战、霍亨甫利得堡会战)。
(二)军队在战区边沿附近占领阵地,等待敌人的进攻,然后自己进攻敌人(如恰斯劳会战、索尔会战和罗斯巴赫会战)。显然,在这种情况下,行动比较被动,等待的时间较长。虽然在真正出现敌人进攻的情况下,采取这种防御方式比前一种方式所能赢得的时间多不了多少,或者一点也不多,但是在前一种场合肯定会发生会战,而在这种场合不一定会发生会战,敌人可能没有足够的决心发起进攻,因此等待的利益也就更大了。
(三)军队在战区边沿附近的阵地上不仅等待敌人进行会战(即等待敌人出现在我们阵地前面),而且还等待敌人真正的进攻(为了引用同一个统帅的战例,我们可以把崩策耳维次筑垒阵地作为例子)。在这种场合,人们将进行一次真正的防御会战;然而,这种防御会战还是可以包括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军队的进攻行动的。象第二种场合一样,这里也根本不考虑赢得时间的问题,但是敌人的决心却要受到新的考验。有的进攻者在发起进攻以后,发现对方的阵地过于坚固,在最后时刻或者只进行第一次尝试以后就放弃了进攻的决心。
(四)军队退入本国腹地进行抵抗。这一退却的目的,是使进攻者的兵力受到削弱,并等待进攻者削弱到不得不自行停止前进,或者至少不能击破我们在他进攻路程的终点对他进行的抵抗。
如果防御者能够在退却中留下一个或几个要塞,迫使进攻者进行围攻或者包围,在这种情况下,进攻者的兵力会受到削弱,防御就会有机会可以以巨大的优势兵力在一个地点上攻击进攻者,这是十分清楚的。
但是,即使没有要塞,向本国腹地退却也能使防御者逐渐取得他所需要的均势和优势(在战区边沿附近他是得不到这种均势或优势的),因为在战略进攻中任何前进都会使兵力遭到削弱,这种削弱一方面是前进本身引起的,另一方面是必要的分割兵力所造成的。我们将在研究进攻时详细阐述这一点。
在第四种场合,首先应该把赢得时间看作是一种重大的利益。如果进攻者围攻我们的要塞,那么我们就赢得了要塞被攻下以前的这段时间,这段时间可能长达几个星期,甚至可能长达几个月。如果前进和占领必要的地点以及路程漫长造成了进攻者的削弱,那么,我们赢得的时间在大多数情况下还会更多,我们转入行动就有一定的自由了。
除了考虑在进攻者进攻路程的终点双方兵力对比的变化以外,我们还必须考虑防御者不断增长着的等待的利益。即使进攻者并没有由于前进而削弱到不能在我们的阵地面前发起进攻的地步,他也可能没有决心发起进攻,因为在这里采取进攻往往比在战区边沿附近采取进攻需要更大的决心。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军队已经削弱,不再是新锐的军队了,同时危险也已增加;另一方面是因为一些优柔寡断的统帅,到达并占领了所到达的地区以后,他们往往就完全放弃进行会战的想法。在这种情况下,固然防御者不能象在战区边沿附近那样充分取得消极结果,但他毕竟赢得了很多的时间。
很明显,在上述四种场合,防御者都可以得到地利;他在行动中还能利用要塞和得到民众的帮助。这些因素的作用是按上述四种防御方式的次序依次递增的,在第四种防御方式中主要是这些因素削弱敌人力量。等待的利益也是按这四种防御方式的次序依次递增的,因此,上述四种防御方式的依次变换应该看作是防御力量的依次增强,作战方式越是与进攻不同,它就越强。我们并不害怕人们因而责难我们,说我们认为一切防御中最消极的防御是最强的。因为抵抗行动并不按上述四种防御方式的次序依次减弱,它仅仅是被延迟和推后了而已。人们可以借助坚固而合适的筑垒阵地进行更有力的抵抗,而且当敌人的兵力由于遭到这一抵抗而损失了一半的时候,就可以对他进行更有效的还击。如果道恩没有利用科林附近的有利阵地,他恐怕就不能取得那次胜利。假如道恩在腓特烈大帝率领不超过一万八千人的军队撤离战场时进行了更猛烈的追击,这次会战的胜利就可能更加辉煌。
因此,可以断言,防御者的优势,防御者所能得到的抵抗力量,将会按上述四种防御方式的次序依次递增,因而防御者的还击力量也会随之增强。但是,换取这些防御利益的代价也是相应地增加的。
如果我们在自己的战区内等待敌人,那么,不论在距边沿多么近的地方进行决战,敌人军队总要侵入这一战区,就肯定不给我们带来损失(除非我们采取进攻,才可以把这种不利转嫁给敌人)。如果我们不是从一开始就采取进攻,损失就会更大一些;敌人所占领的空间就更大。敌人接近我们阵地所用的时间越长,我们的损失就越大。如果我们在防御中接受一次会战,让敌人决定会战和选定会战的时刻,敌人就会长期保持他所占领的地方,这就使我们的损失增大,所以,我们由于敌人不下决心而赢得的时间,是以这种损失为代价的,如果我们向本国腹地退却,这种损失将更大。
防御者所遭受的这一切损失,多半是力量方面的损失。这种损失只间接地(也就是在以后,而不是立即)影响到他的军队,以致人们不能感觉到这种影响。可见,防御者是在牺牲将来的利益换得当前的增强。
如果我们想要考察这些不同的抵抗方式的效果,就必须看一看进攻的目的。敌人进攻的目的是占领我们的战区:或者至少占领我们战区的大部分,而占领几普里的地方在战略上通常是没有独立的重要意义的。因此,只要进攻者还没有占领我们的战区,也就是说,只要他由于畏惧我们的军队,根本没有向我们的战区发起进攻,或者没有进攻我们的阵地,或者在我们向他挑起会战时回避会战,各种防御措施也就可以说是起了显著的作用,我们就算达到了防御的目的。当然,这种成果仅仅是消极的,只能够间接地给真正的还击增加力量,也就是说,它能为还击作好准备,因为进攻者正在丧失时间,而时间上的任何损失总是一种不利,都要受到某种程度的削弱。
因此,在采用前三种防御方式时,也就是说,当防御在战区边沿附近进行时,不进行决战就算是防御取得了成果。但是在采用第四种防御方式时,情况却不是这样。如果敌人围攻我们的要塞,那么,我们就必须适时为这些要塞解围,因此,我们可以以积极行动决定胜负。
同样,如果敌人不围攻我们的任何要塞而尾随我们进入腹地,虽然我们有较充裕的时间,等到敌人极度削弱时才行动,但是,终于要转入行动这一前提始终是不变的。也许敌人占领了作为他进攻目标的整个地方,但是,这只是暂时的,紧张状态仍在持续中,决战还在将来。只要防御者的力量日益增强,进攻者的力量日益削弱,拖延决战就对防御者有利。但是,当等待的利益将殆尽,必然会到来的顶点一出现(即使这个顶点只是由于防御者总的损失产生了最后影响才出现的),防御者就应该采取行动和进行决战。
当然,这个时刻取决于很多的情况和条件,并没有一定的标准,但是我们必须指出,冬季的来临通常可以看作是自然的界限。如果我们不能阻止敌人在他占据的地方过冬,那就意味着我们已经放弃这个地方。不过,只要想一想托里希-佛德腊希这个例子就可以知道,这个规律并不具有普遍的意义。那么,究竟什么是决战呢?
我们在考察中一直把决战想象为会战的形式。当然决战并不一定采取会战形式,它可以是一系列分兵进行的战斗行动,这些战斗行动能够导致剧变,或者是因为真正进行了血战,或者是因为战斗的可能性所产生的效果迫使敌人不得不退却。
根据我们对战争所确定的观点,在战场上不可能以其他方式进行决战。因为,即使敌人军队仅仅是因为缺乏粮食才退却的,这也是我们的武力限制的结果。假如我们的军队根本不存在,敌人军队就一定能设法解决粮食问题。
因此,即使敌人在进攻路程的终点已经被进攻中的种种困难弄得筋疲力竭,并且由于兵力分散、饥饿和疾病而受到了削弱和消耗,也只有我们的武力能促使他退却并放弃已得到的一切,不过这样的决战同在战区边沿附近进行的决战当然有很大区别。
在战区边沿附近进行的决战中,只有以我们的武力对付敌人的武力,只有用我们的武力制服或者摧毁敌人的武力。但在进攻路程的终点,敌人的军队由于劳累消耗了一半,我们的武力在这时所起的作用就完全不同了。因此,我们的军队虽然是决定胜负的最终的因素,但不再是唯一的因素了。敌人的军队在前进中的损失有时可以引起剧变,为决定胜负做了准备,以致仅仅是我们有反攻的可能性就可以促使敌人退却。在这种场合,决定胜负的真正的原因只能是敌人在前进中的劳累。当然,防御者的武力没有起作用的场合是没有的。但是在实际分析问题时,重要的是区别两个因素中哪一个起主要作用。
因此,我们认为可以说,在防御中根据进攻者是被防御者的武力所消灭,还是由于自己的劳累而崩溃,存在着两种决定胜负的方式,也就是说,有两种对付进攻的方式。
不言而喻,采取前三种防御方式的场合通过第一种方式决定胜负,采取第四种防御方式的场合通过第二种方式决定胜负。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在向本国腹地作深远的退却时,才能通过第二种方式决定胜负;同时,正因为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决定胜负,人们才愿意进行这种牺牲重大的退却。
这样,我们就知道了两种不同的抵抗原则。在战史中有一些战例可以十分清楚地把这两个原则区别开。1745年,当腓特烈大帝在霍亨甫利得堡进攻奥地利军队时,奥军正好从西里西亚山区下来,这时奥军的兵力既不可能由于分散,也不可能由于劳累而受到显著的削弱。与此相反:威灵顿在扎里希·佛德腊希的筑垒阵地上,一直等待到马森纳的军队因饥寒交迫而不得不自行退却。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削弱进攻者的并不是防御者的武力。而在另一些战例中这两种抵抗原则相互交错,但也可以肯定其中有一种原则是主要的。1812年的战局中尽管发生了许多的流血战斗(如果在其他场合,发生这么多流血战斗也许就可以说是用武力彻底决定胜负了),仍然没有一个战例比这个战例更能清楚他说明,进攻者是怎样由于自己的劳累而遭到覆灭的。三十万人编成的法国中央军团到达莫斯科时只剩下九万人左右,而派遣出去的却不过一万二千人左右,因而,法军一共损失了十八万七千人,其中战斗减员肯定不超过三分之一。
在以所谓拖延致胜著称的一切战局中,例如在有名的“拖延者”非比阿斯进行的那些战局中,主要是指望敌人通过自己的劳累而崩溃。
总之,在很多战局中这一抵抗原则起了主要的作用,但并没受到人们的重视。只有深入地研究事件本身,才能找到这个决定很多胜负的真正原因。
说到这里,我们认为已经充分阐明了防御的一些基本观念,清楚地指出了各种防御方式和这些防御方式中的两种主要的抵抗原则,并且说明了等待这个因素是如何贯穿于整个防御概念之中,是如何同积极行动密切结合的。积极的行动迟早总要出现,而当它出现时,等待的利益就不存在了。
至此我们已经从总的方面分析并研究了防御的问题。当然,防御中还有一些十分重要的问题,包括要塞、营垒、山地防御、江河防御和翼侧活动等的实质和作用等问题,我们准备在以下各章加以论述。所有这些问题并没有超出上述一系列观念的范围,只不过是这些观念在具体地方和具体情况中进一步的运用而已。我们把从防御的概念和防御同进攻的关系中得出来的观念同实际联系起来,就指出了怎样才能从实际中再回到那些简单的观念上来,也就是说,能够找到可靠的根据,以免在讨论问题时求助于那些本身毫无根据的论据。
然而,战斗的组合是多种多样的,尤其是在有可能发生流血战斗但实际上没有发生,就产生效果的情况下,武力抵抗在形式和特点上有很大的变化,因而人们很容易认为这里一定还有另外一种产生效果的因素。在简单的会战中流血抵抗所产生的效果同战略计谋所产生的效果差别很大,因而人们必然会认为还有一种新的力量介乎这两者之间,就象天文学家根据火星和木星之间空间广大而推论出还有其他行星存在一样。
如果进攻者发现防御者据守着一个坚固的阵地就认为自己无法攻下,如果进攻者发现防御者有一条大河作掩护就认为自己不能渡过,甚至担心在继续前进中自己的给养不能得到保障,那么,只有防御者的武力,才能引起这些效果。因为进攻者害怕在主要战斗中或者在一些特别重要的地点上被防御者的武力击败才停止前进,只是他不愿承认罢了。
我们承认在未经流血战斗而决定胜负的场合,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那些虽未真正进行但已作了部署的战斗,在这种场合,安排战斗的战略计谋,应该被看作有效因素而并不是战斗在战术上的胜负。而且当人们谈到使用武力以外的其他防御手段时,他们所指的只是战略计谋所起的突出的作用。但是,如果说一切战略计谋必须以战斗中的战术成果为基础,那么进攻者一定会针对这个基础采取有效的措施,使自己在赢得战术成果方面占有优势,以便随后彻底粉碎防御者的战略计谋,这始终是防御者所担心的。因此,决不能把战略计谋看作是某种独立的东西,只有人们有某种根据肯定能取得战术成果时,战略计谋才能发挥作用,象拿破仑这样的统帅能不顾一切地冲破敌人的全部战略计谋而寻求战斗,是因为他从不怀疑战斗的结局将对自己有利。由此可见,只要战略没有完全以优势兵力在这种战斗中压倒拿破仑,而去致力于玩弄比较精巧的(无力的)计谋,它就会象蜘蛛网似的被撕破。但是,象道恩这样的统帅,就容易被战略计谋所阻止。因此,企图以七年战争中普鲁士军队对付道恩及其军队的办法来对付拿破仑及其军队,那是愚蠢的。因为拿破仑非常清楚地知道,一切都取决于战术成果,并且确信能取得战术成果,而道恩却不是如此。因此,应该指出:任何战略计谋部只能以战术成果为基础,无论是否通过流血的途径解决问题,战术成果都是决定胜负的真正的根本原因。只有不必担心胜负决定时(不论这是由于敌人的特点或敌人的情况,还是由于双方军队的精神的和物质的均势,甚至是由于我军占有优势的缘故),才有可能从战略计谋本身得到利益。
从全部战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战局中进攻者没有进行流血决战就放弃了进攻,因而,可以说战略计谋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可能使人认为,至少这些战略计谋本身就有巨大的力量,而且当进攻者在战术成果方面不占有显著的决定性的优势时,战略计谋就大多可以单独解决问题。我们认为,这一观点是错误的;许多进攻所以没有发挥作用,其原因存在于战争的较高的关系中,即存在于战争的政治关系中。
产生战争因以及形成战争的基础的总的关系也决定着战争的特点,这些总的关系使战争中原来的敌对感情由于必须通过各种复杂的关系,变成非常微弱的因素,这一点在采取积极行动的进攻的一方当然表现得更为明显,更为突出。只要稍加压力,软弱无力的进攻就会停止下来,这自然是不足为奇的。对付一个脆弱的、为重重顾虑所削弱了的、几乎已不存在的决心,往往只要作出抵抗的样子就够了。
因此,防御者所以能用不流血的方法多次取得成功,并不是由于存在着坚不可摧的阵地(这是到处都有的),并不是由于进攻者怕横贯在战区的林木茂密的山脉和穿过战区的宽阔的江河,也不是通过某些战斗组合瓦解敌人,而在于进攻者意志薄弱,踌躇不前。
我们可以而且必须考虑上述这些抵抗力量,必须恰如其分地认识它们的作用,但不应该把其他事物的作用归之于它们的身上。我们不能不强调指出,如果批判者不站在正确的立足点上,那么战史关于这方面的叙述就会很容易成为不真实的和带有欺骗性的记载。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没有采用流血的方式进行的失败的进攻战局。
进攻者进入敌国,迫使敌人的军队后退一段距离,但对进行一次决定性会战却犹豫不决:于是他在敌人面前停下来,好象他已经完成了占领的目的,他的任务只是掩护已占领的地方了。好象寻求会战是敌人的事情,好象他自己每天都愿意进行会战似的。这一切都是虚伪的借口,统帅借以欺骗他的部下、宫廷、世界、甚至他自己。真正的原因是他发现敌人过于强大。我们这里说的不是指这样一种情况,进攻者放弃进攻是因为他不能利用己取得的胜利,是因为他在进攻路程的终点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开始一次新的进攻。这样的情况是以有一次成功的进攻,即真正的占领为前提的。但我们这里指的则是进攻者还没有达到预定的占领目的就停顿不前的情况。
这时,进攻者就进行等待,以便将来利用有利的情况,但是预定的进攻已经证明,最近的将来不可能有更大的希望。因此,这种有利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这也是一个虚伪的借口。如果这次行动象常见的那样,是和同时进行的其他行动有联系的,那队就会借口支援不足和协同不够,把自己不愿意担负的任务推到其他军队身上。它会摆出种种不可克服的困难,并在各种复杂微妙的关系中寻找理由为自己的无所作为辩护。进攻者的力量就这样消耗在无所作为之中,或者更确地说,消耗在不彻底的因而没有成果的活动之中。防御者却赢得了非常宝贵的时间,气候恶劣的季节临近了,进攻者退回自己的战区进行冬营:进攻也就随之结束了。
这一整套虚假现象都被载入了战史,掩盖了使进攻者没有取得成果的最简单的和真实的原因,即畏惧敌人的武力。如果批判者想研究这样的战局,那么他就会被许多相互矛盾的毫无根据的原因所迷惑而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而人们又没有去探索事情的真实情况。但是,这种欺骗不仅仅是一种恶劣的习惯,而且是很自然会产生的。那种削弱战争威力,也就是减弱攻击的牵制力量,大都存在于国家的政治关系和政治企图中,人们总是把这些关系和企图隐蔽起来,使世界、本国人民和军队无法知道,在许多场合甚至使统帅无法知道。例如,任何人都不会也不愿意承认,他决定停止或放弃行动的原因是担心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坚持到底,或者是怕招致新的敌人,或者是不愿让自己的盟国变得过于强大等等。对所有这类事情人们都长期甚至永远保守秘密。于是统帅为他自己或者为他的政府着想,只好编进一套虚假的理由以解释事件的来龙去脉。在军事问题上进行辩论时反复出现的这种欺骗手法在理论上已经僵化成一些体系,这些体系当然是同样不包含什么真理的。只有象我们力图做到的那样,沿着事物内在联系的简单线索进行探索,理论才能弄清事情的真相。
如果以怀疑态度来观察战史,那么,种种关于进攻和防御的空洞理论就会不攻自破,而我们在这方面提出的简单观念就会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因此我们认,这个简单观念适用于整个防御领域;人们只有完全掌握它,才能够十分清楚地弄清大量的事件。
现在我们研究各种防御方式的使用。
这些防御方式一个比一个有力量,那是用一个比一个大的代价换来的。如果没有其他条件的影响,统帅会因此选择适当的防御方式,既能使他的军队具有所需的抵抗力量,又能使他不致退得过远,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但是,必须看到,选择这些防御方式时大多受到很大的限制,因为防御中出现的一些重要条件必然会迫使统帅选择某种防御方式。向本国腹地退却需要有辽阔的国土,或者要具有象一八一零年的葡萄牙那样的条件,当时有一个同盟国(英国)作它的后盾,而另一同盟国(西班牙)的辽阔的国土大大地削弱了敌人的攻击力量。要塞的位置更多是在边境附近,还是更多是在本国腹地,同样可以决定是否采取这样的计划,而国家的地理和地形状况、居民的特性、习俗和信念则起更大的作用。选择进攻会战还是防御会战,则应根据敌人的计划,双方军队和统帅的特点来决定。最后,是否占有特别有利的阵地和防线也可以决定防御方式的选择。总之,防御方式的选择在很多场合更多地决定于这些条件,而不是单纯的兵力对比。这里提到的这些最主要的条件我们还要作进一步探讨,因此它们对选择防御方式的影响也要在以后才能更明确地加以阐述,最后,在《战争计划和战局计划》那篇里,我们再把这一切总括起来探讨。
但是,这种影响大多只在兵力相当的情况下才起决定性作用,在兵力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兵力对比起着主要的作用。战史充分证明,人们并没有根据我们在这里阐述的一系列观念,而是机智地通过迅速的判断,根据兵力对比选择防御方式,同一个统帅,同一支军队,在同一个战区,这一次挑起了霍亨甫利得堡会战,那一次却在崩策耳维次扎营。至于说到会战,就连统帅中最喜好进攻的腓特烈大帝,在兵力十分悬殊时也终于认识到必须占领真正的防御阵地。拿破仑以往象一只野猪似地冲向自己的敌人,可是一八一三年八-九月间,当兵力对比的变化对他不利时,他就象栏中的野兽那样东碰西撞,而不是勇往直前地向其中某一个敌人开火了,这一点难道我们没有看到吗?但同年十月,当兵力悬殊达到极点时,他就象一个人在房间背靠墙角那样,在来比锡附近,在帕尔特河、埃耳斯特尔河和普来塞河所构成的角落里寻找掩护和等待敌人,这种情况我们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我们不能不指出,本章比本篇其他任何一章都更清楚地表明,我们的目的不在于提出作战的新原则和新方法,而是探讨久已存在的东西的内在联系,并弄清其最基本的要素。


 微信登录
微信登录